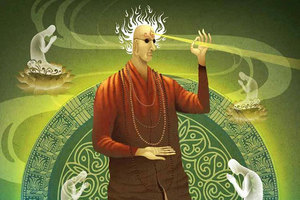宋丹丹小品里,夫妻倆調情,女人指責男人盡給她看鬼片,“嚇得我直往你懷里鉆”——這可能是恐怖/驚悚片選擇跨年檔和情人節檔期的動機之一,當然,真實的原因是,恐怖/驚悚片是少數能夠盈利的電影品種,怎么著都得放個好檔期,暑期檔是禁 區——要保護青少年,只有放在跨年檔和情人節了。那么,中國人不忌諱嗎,大過年的放這個?因為,我們的恐怖片里,不會有鬼。
輕度的、可控的恐懼,未必是居家旅行必備良品,卻也是不可或缺的生活調料。《恐怖:起源、發展和演變》里說,恐懼感來自扁桃體中神經細胞間微小的纖維鏈扁桃體,扁桃體“確如輪軸一樣是恐懼之輪的核心”,一個人,如果老是天不怕地不怕,多半是因為患有扁桃體反應缺乏癥。這么說來,恐懼是天賦的,由身體里的硬件造成,天然合法。合法的情感,當然需要激活,需要釋放。恐怖片正擔此任。

我們從前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恐怖片,但,恐懼情緒必須要有個紓解的渠道,于是,上世紀80年代,恐怖片通過兩類電影,體面地借體還魂,其一是“反特片”,恐怖片里應有的一切,這里都有:女尸、慘叫、雷雨之夜、撲在窗子上的黑影、黑色橡膠雨衣、口罩后的眼睛、黑洞洞的槍口、陰森森的古剎、幽暗的地道。另一種,是以公安干警破案為主題的“驚險片”,故事動機,往往是奪寶或者尋找動亂年代的余孽,這類電影里,最經常出現的反面形象,不是走私集團頭子——大部分時間他們偽裝得很好,而是醫生或精神科醫生,他們常常在雷電交加的晚上,用給牲口打針的特大號針筒,給受害者打迷藥。精神科醫生昂秋青和舒偉潔后來合寫了一本名叫《恍惚的世界》的電影書,大力譴責這種妖魔化。
這時候的恐怖片,處處都有現實的烙印,恐怖得太老實了,恐怖得太此時此刻了,人們漸漸不滿足了,轉而追求更具普遍意義的、更空靈些的恐怖,1989年,《黑樓孤魂》出現了,以現代社會為背景,而且當真有鬼。給它撐腰的,是80年代后半段的狂歡氣氛,那些直接以錄像帶形式發行的影像制品里,什么都有,鬼怪、連環殺人狂、色情。在《紅樓夢》里演過探春的東方聞櫻,一走出大觀園,立刻投奔怒海,或監制或出品,炮制了許多錄像片;范美忠從前供職的光亞學校的校長卿光亞,提起自己的發家史,也并不隱瞞——拍錄像片,“半裸的野人跳啊跳那種”;我的朋友H至今也對他看過的兩個國產錄像片津津樂道:一個講的是落到地球叢林里的半裸的女外星人,用安裝在頭上的激光發射裝置,消滅迫害她的野人的故事,另一個是一個野人和警察在火山口烤骷髏頭。現代社會的電影里應該有的,在彼時的錄像片里全都出現。
沒猖狂多久。90年代旋風一般地來了,90年代,是光潔整齊的烏托邦,有大量光潔整齊的高樓為證,80年代的這些事,立刻成了語焉不詳的史前文明,鬼怪更是龐雜污穢的東西,沒能進入這個光潔的時代。《電影管理條例》、《電影劇本(梗概)備案、電影片管理規定》里,暴力、恐怖、靈異,都是必須要刪減修改的元素。
恐怖片還是要有的吧,既然不能鬧鬼,內地拍的,或者進入內地的恐怖片,只好鬧人,或者是裝鬼,或者歸為幻覺、夢境、精神疾病。鬧鐘響了,或者醫生冷冷地說“你該吃藥了”,成為最經常的結尾。
《閃靈兇猛》、《兇宅幽靈》在極盡鋪張的鬼影重重之后,都給出了現實的解釋,而彭氏兄弟的《見鬼2》,在香港上映時是有鬼的,內地上映的版本里,被修改為心理問題,此外還有徐克的《深海尋人》,精神問題解釋了一切。怪力亂神電影,由此成為一種智力考試,像一種酒桌游戲,說什么都可以,就是不能說“你、我、他”,影人要在不能說出那個字的情況下,制造恐怖,像在沒有雞蛋的情況下,做出一碗雞蛋湯。
不過,又何必看恐怖片呢,要釋放恐懼情緒,我們的社會新聞,是更好的地方。新疆黑工廠,遠比《得州鏈鋸殺人狂》要恐怖,所以,事情可能是這樣的,當社會問題無法管理的時候,就得著重管理情緒,既然沒可能刮骨療毒,剪掉箭尾也是好的。